《坛经》神秀偈
发布时间:2023-04-24 09:08:47作者:法华经讲解网
《坛经》神秀偈
刘楚华
一
敦煌本发现以前,流布本的《六祖坛经》是长期以来了解早期禅宗历史的惟一资料,舍《坛经》以外比较全面而可靠的,要算宗密(?~841)的《禅源诸诠集都序》及《圆觉经大疏义钞》,已是9世纪的文献了。30年代由胡适、铃木大拙等带动的禅学讨论,是本世纪禅史研究热的第一峰,其后随着敦煌禅宗史料的整理和开放,大家对早期禅宗史的认识更加全面。
例如敦煌本《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成立于780年,时慧能(638—713)已谢世60年,学者公认它是目前可见最古《坛经》本,不论从文字、内容都是最迫近慧能本人思想风格的记实。而敦煌北宗及早期禅宗文献,也补充说明了历史真相,这些文献的撰述人多为禅门第七至九代传人,即神秀弟子或再传弟子一代,其写定年代与敦煌《坛经》本接近,甚或有更早者。其中有五祖弘忍(601—674)弟子玄颐之下的净觉(688—746),撰《楞伽师资记并序》;法如(637—689)一系所传的《传法实记》,神秀(606—706)下传的《无生方便门》。这一系列文书写在8世纪初至中后期,正南北宗争持、北宗未衰、南宗发展之时,除了说明东山门下不同枝脉的具体情况、南北争统、血脉谱系等课题外,这些材料,正补充了《坛经》中不够完整的北宗思想面貌,从这一点说,也可以说成是慧能对北宗神秀禅批判的最可靠注脚。
大家耳熟能详的能秀法偈,主要来自通行本。诸版本《坛经》之间文句颇有出入,敦煌本的慧能偈作有二首,流行本《坛经》则合为一首。至于神秀偈一首,诸本差别不大;一则因各本偈义统一,二则《坛经》中神秀偈到底是慧能偈的陪衬,为此之故,过去学者讨论焦点多在能而不在秀。陈寅恪先在《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中,指出慧能偈义有附会之处,主要缺失在:一)譬喻不适当;二)意义未完备。其看法如此:上半首身心对举,而以菩提树比变灭无常之肉身,于义不合,所以说譬喻不当。其次,即使比喻适当,其下半首偈义只言及心而未及身,仅得文意之半,所以谓意义未完备。50年后,任继愈先生在《敦煌坛经写本跋》又指出:神秀偈强调主观修习,以坐禅调练身心,极力防范污染;能偈则强凋佛性本来清净的信念,树立“佛性本来清净”的宗教世界观,而菩提树与明镜台是比喻,不一定算作意义不完备。陈先生从修辞角度观察,任先生从能秀二师的禅教取向上着眼。此两种观点方法,当可以容通,文意畅顺,方便教理通达。本文试顺陈先生的修辞角度观察,尤其比喻的运用上着眼,参检北宗文献,再解读传法偈义。
敦煌本神秀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莫使有
尘埃。
凡宗教文学都广用比喻说理,佛经说法更使用大量譬喻修辞。从最基本的文学修辞原理看,比喻来自生活体察,所采用喻体,每取其与本体相似的性质,否则不能成立。先看神秀偈,以菩提树喻身,是否取譬不伦呢?这得先看所说的是什么“身”及其与喻体“菩提树”的性质是否相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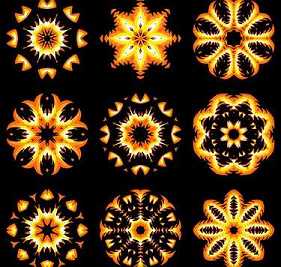
菩提树原产印度,佛祖于此树下静坐思惟七七四十九日,终证道得平等正觉,因以名之,又名“思惟树”。今看所有俗名,菩提树、思惟树(Bodhi tree,Ficus religiosaLinn)命名都已涵有文化意义,取用为譬,自然连系到宗教历史,令人联想到此树下证觉的佛陀。
菩提树的植物学说明是:桑科,常绿大乔木,高10—20米,叶革质……原产印度,亚洲南部广为栽植,分布我国南部各区广东及云南南部一带。《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即毕钵罗树也……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叶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
对于佛教徒而言,菩提树有另一种用处,它的子实坚硬(俗称金刚子),可以作念珠,珠面有大圈文如月周罗,细点如星,谓之星月菩提,持之数诵福德无量。然则叶常绿不凋、子坚实不朽的植物学生态,可以引起相应的宗教联想,即采用此物为譬,必有所指的喻意。如偈句所说,用以比某一种“身”,似非偶然拼合所成。
陈先生文章说:“可知菩提树为永久坚牢之宝树,不能取以比变灭无常之肉身。”用菩提树比肉身、色身,固然有不伦之病,加上偈句简单,对本体“身”和喻体“树”都没有清楚的限定说明,容易令人生疑。假使此“身”不指色身,而指永久坚固的“佛身”,则偈义可以成立。佛经常用什么比喻说“色身”呢?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电,应作如是观。”
维摩经方便品云:“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
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焰,从渴爱生。是身如芭

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
虚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响,属诸因
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
常用不坚易坏的事物比喻诸法无常,色身是无常法,因缘所造,缘聚则合,缘散则灭,易朽是其本质。上述维摩经的十喻,还加了说明,故喻意十分明白。大乘经典也谈到有佛身。佛有三身,一是由父母生身,即“目净修广如青莲”,有八十种好的佛报身,另一是得证解脱、永恒不坏之佛法身。方便品又云:
佛身者即法身,从无量德智慧生,从戒定慧生
……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
佛法身不是存在体,而是指绝对真理实体。大乘佛教对佛三身的术语有不同释义,但以佛法身为常住不朽,是大小乘各宗的共识。本来大乘佛教认为,佛法身寂灭,无相可得,不可以声音色相言说求之,然而,说法时可以采用声音色相为譬喻,此为权宜方便。记浅训深,托此明彼,是佛教说法广用的手段。
如此说来,以菩提宝树不朽之质,比喻法身不生不灭的体性,就不能说不类了。那么,神秀说法曾作此取譬吗?敦煌文书存神秀的开法实录。
1.《大乘无生方便门》,其中“第一总彰体”之“离念门”下记:
“是没是佛?
佛心清净,离有离无,身心不起,常守真心。
是没是真如?
心不起心真如,色不起色真如,心真如故心解
脱,色真如故色解脱;色心俱离,即无一物,是大菩提
树。”(大正藏2843页273下)
2。《大乘五方便宗》:
“……行住等看,不住万境。台身直照,当体分
明。
问:看时,看何物?看看,看无物。
阿谁看?觉心看,透十方界,清净无一物,常看,
无处相应即佛。
豁豁看看,看不住,湛湛无边际,不染即是菩提
路,[……缺]
心寂觉分明…”(伯希和2058)
(无题):
“[上缺……]身寂则是菩提树……”(伯希和
2270)
此中所记正是慧能所诃的看心看净为入门引导,常坐不动禅定法。其法要在止息妄想、离念,解用《起信论》,取其中“一心开二门”义,将佛心分解为二。一是离念门,离念则觉,即佛如来平等法身;二是众生门,有念即不觉,坠于众生心识流转,一净一染,一解脱一生灭。两两分明,是神秀重分解的理论风格。实践方面,神秀引导坐禅人看心、不断看净心,不起识心,见境不起妄念,不作意分别,由“离念”人定,由定发惠,自可看见佛性本净。慧能所诃责者,正是此看心看净的坐禅形式,谓“禅非坐卧”,坐是病,和反对他理论上将定惠、佛心人心等作二元化的理论设施。此暂不详论,且回说用喻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神秀于法坛上引导学禅人坐禅时,或者在解说教义理论的纲领时,实际上引用了菩提树的比喻,而所比的本体是佛清净的“法性身”而非指缘生的色身、肉身。菩提树是神秀依《起信论》开章明义,解说教理最核心理念——佛心本体时所常用的设譬。
在禅宗问题谈文字修辞,最容易犯文字言教的违。广义的“不立文字”标志,在禅门不自慧能始,达摩以下历代都强调离言说相。东山门下,尽管神秀是学院气息较浓厚的一支,重视通经,仍强调灵活随机解说,神秀所谓“方便通经”是就经典文句,自由地说理,开放地引申;他用五部经论为教学纲领:《起信论》为首脑,其余为《法华经》、《维摩经》、《思益经》及《华严经》。也强调不重文句义疏,重视心证、坐禅实践。《楞枷师资记》说五祖“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又以《楞伽经》传弟子,谓:“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神秀也不出文记,持受楞伽为心要,这种语言态度,显然是东山余绪。禅宗、经典文字的疏解方法是开放的,名相释义也是自由的,如果从一般意义的修辞角度看,南北宗态度同,而程度或有深浅。其后南宗标榜严格意义“不立文字”,进一步摆脱经论束缚,相较下,北宗就形于保守教说了。
南宗之进一步标“不立文字”的旗帜,可以说是对佛教传统的文字教说和学理权威的反动,慧能不识字,唯能解金刚、法华经义,通解名相。如《坛经》说:
“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真如,但无妄念,性自清
净。”
又说:
“自性常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
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一时
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
解说用喻仍带有一点东山楞伽经的痕迹,不过也是按己意解说,把佛性与人的自性完全等一,理论更简化,单刀直人而已。慧能教弟子说法,提出“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的法则,又“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借“不著二边”的中道法,辩证地、机活地使用语言。试看慧能的说理,用生活语言,不引经句,修辞朴素,用大量生动比喻。文义简单,而层次分明,正合“不离性相”的原则。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彼岸到,解
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即是于此岸。离
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罗
蜜。”
“邪心是大海,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
鱼鳖,虚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
十善是天堂……除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
害除,鱼龙绝……”(《坛经》)
上面例子中的喻体,不止为了说明本体的性质而施设的形象陈述,且是推理过程中的有力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北秀南能在说法手段既合一般修辞原理:比喻本来就不限一体,可以随体多变;另一方面,称离言说相,实不可能尽弃言说,所谓解用通经、指事问义,取譬说理,都强调自由灵活,两人都继承了东山门下活用语言的修辞本色。
佛经解说“佛心”的形象比喻十分丰富,明镜、净水、琉璃、摩尼珠、日光、月光、火炬是最常见,极言佛心本光明清净。查敦煌北宗文书中以上各种比喻都可见,由《大乘五方便》所记,神秀依一般佛教开坛仪式:发愿、忏悔、授戒、坐禅,实况如下:
“……次各称已名忏悔罪言……我今至心尽忏
悔,愿罪除灭,永不起五逆罪障重罪,如明珠没浊水
中,以珠力故,水即澄清,佛性威德亦复如是,烦恼浊
水皆清净。汝等忏悔竟,三业清净,如净琉璃内外明
澈,堪受净戒……。”
谓身口意三业罪除,恢复本来佛性,明净如明珠,清澈如琉璃,与明镜的喻意相同。查记神秀开法的文献,明镜之喻不多见,而是其他出自秀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的北宗文献,明镜之喻彼彼皆是,试举数例。
1)张说为神秀作铭,概括他的禅学为“心镜外尘,匪磨莫照”。
2)净觉曾受神秀禅法,所撰《楞伽师资记》(大正藏2837)记禅门历代师说,明镜之喻特多,如宋求那跋陀罗下:“大道本广遍,圆净本有,不从因得。如似浮云底日光…亦如磨铜镜,镜面上尘落尽,镜自明净。”
又如道信禅师下:“正如来法性之身,清净圆满,一切类悉于中现。而法性身,无心起作,如颇梨镜县于高堂,一切像悉于中现,镜亦无心,能现种种。”
又普寂禅师下:神秀传法多人,普寂等四弟子,“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
对北宗人来说,传灯传镜,同为禅门传法的比喻。
3)题为“忍和尚”撰的《最上乘论》,亦以磨镜为五祖所传“守本真心”禅法的比喻。“我既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净,如云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亡念云尽,慧日即现……如磨镜尘尽,明自然现……”
“念念磨炼莫住者,即自觉见佛性也。”
由此看来,神秀的磨镜拂尘,是东山传法。不过,他除了持弘忍所授楞伽经义之外,更加入了《起信论》为主导理论。那么,神秀等诸楞伽禅师及其门下用镜喻心的惯例,就可以理解了。
《楞伽经》说众生本具佛性,就以明镜比喻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第八识)。镜中影像,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因为识心(前七识)遇外境、起念攀缘,呈现虚妄假像,是不真实的。修行人当磨镜尘,断妄想,见镜体清净,证自觉圣智。
《起信论》亦云:
“诸佛如来离于见想无所不遍,心真实故……诸
佛如来法身平等遍一切处,无有作意故。而说自然,
但依众生心,现众生心者,犹如于镜,镜若有垢,色像
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现。”
此处所言法身是从理上说,若从心说就是如来藏识在觉的本来状态。觉即是佛心;同一心若坠于不觉,即是众生心、识心、妄心。净镜比佛觉心,《起信论》更再细分四种“觉心”的性相,所谓如实空镜、因熏习镜、法出离镜及缘熏习镜。(大正藏1666页576下)
可见东山法门至神秀北宗的镜喻修辞,一与沿用的经典术语有关,二与经典连系的信仰理念有关。其中最关键理论在:1)佛性论:众生心与佛心的理论关系及其中包涉的心理认识。2)宇宙本体论:真如本体缘起的世界观。整北门的拂尘磨镜工夫理论和实践,都由此基础展开。本来,由达摩壁观以来,都重实践,少言说。到了唐代,东山法门在学院理论和重视文字翻译的时代氛围下,不免加强了《楞伽经》为教理标志,神秀又参入《起信论》,其重学理分析的经典倾向,又比弘忍要明显一些。
此种倾向应当一直维持,到普寂门下一代不改。神秀死后50年间,南宗崛起,一方面禅门南北对峙之势已成,另一方面禅人南北转学的情况普遍起来。疑是北人投南的沙门慧光所撰的《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推测当成立于8世纪中叶左右,且明白是北宗理论。带浓厚起信色彩,其中解说佛法身,仍引用起信的“觉”义。此外又疑,更渗入了法相宗的八识阿梨耶的“大圆镜智”。可见一门宗教理论说法修辞,有一定的纵向承袭,又不能不考虑横向的时代习染。神秀及其门下,在北方佛教文化中心正值华严、唯识全盛期,不可能全不受影响。
总看神秀偈上半首身心对照,显是同属“佛心佛性”理论层,并无对立相反之意。众生本有此佛性,只为客尘所障而已。菩提明镜同举,并不违大乘教义,且更符合早期禅学理论和修辞习惯。何况明镜之喻心,可以说普遍适用于不同宗派的理论,此镜印度佛用之,中国佛用之。不唯如此,道家至人用心亦若镜,荀子以水镒须眉,比心之清明察理;西方哲学家何尝不用镜指喻永恒的上帝,喻光洁的灵魂,以磨镜工夫比追求真实主体,喻洁炼灵魂?明镜,自从人类发现鉴照的功用之后,就用以比拟心灵光辉的折射,意浅义明,是不同文化系统都乐用的比喻。
四
就神秀上下文意检看,起句“菩提树”真如法性身,是对永恒不坏的真理本体的陈述。先置于“心一镜一尘”之前,故不影响推理结构的完整性。且法身自体圆满,对它只有礼赞和描述,无工夫设施可言。“拂拭”以下二句是承“明镜”句,专言修心工夫,劝常勤拂拭,使保清净,不沾染客尘;染则因缘生灭,净则见清净如来。全偈意思完备,不但自圆其说,亦不违于教义。
据南宗的看法,神秀偈的最大缺失在哪里?弘忍的评价是“见即来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缺失不在文意而在理论见地不彻底。如果就佛性本来清净的内容理解和众生本具有佛性的信念来说,是大乘共有的认识,南北宗基本一致。所以法偈起首二句“身心”的陈述,似乎体现不出南北观点的歧扎,学者也多就后阙讨论,认为差别在拂尘的工夫。不错,慧能反对神秀看心看净的坐禅形式,但是修行方法离不开理论,慧能如果要取消弘忍所传的守心看净坐禅法,而提不出相应的理论批评,则不能体现他在禅学改革上的进步意义。慧能偈的两次回应,首两句句义不十分一致,游离在菩提有无树,明镜有无台之间。但是,无论身是不是菩提树,心有没有明镜台,慧能偈二首都一致质疑“何处有尘埃”?
如上文所说过的,神秀的拂拭尘埃是有理论依据的。“尘埃”在《楞伽经》中是颇重要的譬喻,比指存在于众生界的事物。在宇宙生成论的层次,楞伽属自性缘起的系统,如来藏心体是一切生灭存在(法、尘)的本源;从心理分析的层次看,众生虽然理论上之本具佛性,作为有心理意识的存在,前七识的起作与外尘的结合遮盖了本性,所以要有“息妄离念”拂尘的工夫。《起信论》在《楞伽经》的理论上分解地把“真心”析为“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一净一染,神秀的实践方法也是离染看净,返本照源的路。慧能提出“直指本心”的口号,革命意义在于把佛性与众生本心本性自性之间的理论说明也省略了,谓“本性是佛”“佛是自性,莫向身外求”,当前的众生心就是佛心,众生是佛,完全没有距离,无分净染。虽然理论上没有本质的改动,只是高度简化了设施,单刀直入。工夫上也无程序设置,自性迷是众生,自性悟是佛,关键在见或不见,只要在生活中常见自性,“不识本性,修行无益”。彻底取消坐禅的工夫程序之同时,也相应地取消了理论的步骤。理论简易,对远离佛教学术中心的南方,对非知识阶层的信众,正是慧禅的魅力所在。工夫直捷,把印度输入的达摩壁观禅,简化为生活禅。就这些特点,慧能树立起严格意义的中国禅宗本色。这是南宗革命意义之所在。
再看敦煌本慧能偈:

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本清净,何
处有尘埃。
二、(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明镜本清
净,何处有尘埃。
(原文“心是菩提树,身如明镜台”)
上两偈文意有病吗?“佛性常清净”与“明镜本清净”句,再正面申述佛性的性质,既重复上句明镜的命题,有套套逻辑之嫌,修辞上也有重赘的毛病,又显不出慧能“自性是佛”的主张,所以后来流布本就不再出现了。经过南宗弟子的集体努力,流布本《坛经》的慧能偈修正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
惹尘埃。”
前三句句义都不算明确,首二句反驳神秀偈,只但涉及神秀偈中的喻体部分。第三句也是反遮句,“本来”指什么呢?此句指涉句义主体不明确。不过在这个情况,模糊的修辞,反而有较阔的理解空间,文意是承上两句,可以说是提明镜中本无尘埃,也可说说世间一切法虚空不实,本来无有一物,不但明镜中的影子不真实,明镜自己亦不真实。一切法空,无所谓镜、尘之别,则拂拭的工夫就变得多余了。后两句既指向神秀的本体论结构,也涉及人性的心理设施,含意丰富,而带有般若空理的色彩,更接近慧能的风格。“何处有尘埃”句既破神秀的“客尘”,兼诃他的拂拭工夫。而且以疑问作结,引发思考,是好句,所以宋以后《坛经》各版本都保留了。
由敦煌本到流布本的《坛经》,慧能偈法偈,长期经过门下弟子的修正,文句通畅,文意趋向也完备了。
五
能秀二师不出文记,《大乘五方便》和《坛经》均是门人所述,能秀法偈不出于二人之手,最可能是弟子所造,自不必多论了。本文提不出什么新看法,只是用了北宗神秀门下的资料,解读神秀偈,证明无论作者是谁,神秀偈义完整,使用了北门的习惯用语,而且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北宗禅的人门路径。
慧能偈,经过门人长期润色修正,较晚完成。敦煌本《坛经》成立之前,神秀偈已定形了,它的成立时期当在8世纪中叶。当时普寂(651—739)的弟子一代在北方仍活跃,早在慧能生时已有北人南下求学(如《坛经》中的志诚即是),此时,交流风气当更普遍,南人对北宗的批评亦趋激烈,对当时北宗的教学情况必充分掌握。假设神秀偈果是南人所作,以南方常见的菩提树为譬,批判神秀由净坐人菩提、由拂尘见佛性的形式主义,批判对象虽然是神秀,模仿的是神秀门人传法情况,基本没有脱离事实。
宗教文学修辞和宗教术语、宗教哲学理念的关系很微妙。一个宗派表达它的思想,有特用的概念、修辞风格、宣传标志,在它成熟时期,它们的关系是统一的,在它的形成阶段,会有变化发展或者不一致之处,或承袭旧说,或推陈创新。禅宗标榜不立文字,在宣传本宗禅法时,则大造法偈。读《坛经》的神秀慧能法偈,比较二者的修辞特点,也可以见其中一二端倪。



